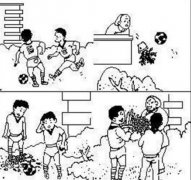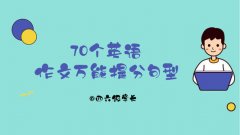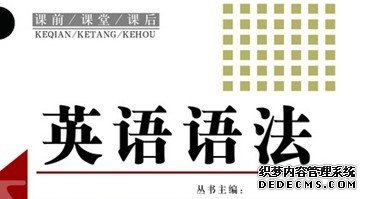幼教论文:现代幼儿健康的生态学审视
幼教论文:现代幼儿健康的生态学审视
内容提要:运用文献资料与逻辑分析法,从生态学视域探究现代幼儿健康的藩篱及突破策略。研究认为:家长对幼儿过度呵护、管制与心灵漠视,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幼儿健康成长的环境。后现代主义的生态学理论使当代幼儿突破健康危机成为可能,首先,幼儿要脱去成年人冗繁的遮蔽,亲近自然,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次,要营造一个健康的生态自然环境,并依据幼儿的年龄与性格特点来不断调适其周围的物件环境;第三,成年人应以“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原则,来处理、解决幼儿成长中的问题。
关 键 词:幼儿健康 生态学 现代社会 生态环境
基金项目:2014年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890019)、华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
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身体的健康,一切将无从谈起[1]。然而,近年来我国幼儿体质与适应环境的能力逐降,健康问题突出[2]。纵览2000年起的三次国民体质监测,幼儿(3~岁)身体形态数据均值增长,但身体素质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3]。同时,存在认知、行为、情感交流等障碍的幼儿数量亦有增加趋向[4],家长普遍抱怨现在的孩子愈来愈难养,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越来越差。如何化危为机,增强当代幼儿的综合健康水平,实现幼儿“身体”的救赎,已成为家长、幼儿园乃至整个社会迫切关注的问题。
培养“体、智、德、美全面协调发展”[]的幼儿教育文件指南,一改往日“德、智、体、美”的表述,“体”成为了幼儿教育首当其冲的关键字;此外,现实中保育幼儿的硬件设施亦在逐步优化,教师学历趋向提高,教育理念渐进发展,且幼儿在当代家庭中享受着教育、饮食、卫生的优先权。然而,如何解释在此环境下成长的幼儿出现身体、心理、社会适应能力等健康水平的持续下降呢?从生态学(Elgy)的视角审视幼儿生活的场域,随之发现影响其健康的本体:即当代社会飞速发展中所附加的“熵”,对幼儿健康带来的威胁与侵蚀越发严重。该研究试图从幼儿成长的生态学角度切入,提出影响其健康的问题,进行逻辑分析论述,并依此来研推幼儿健康促进的方式与方法。
1 相关概念的理解与界定
1.1 幼儿
意大利著名幼儿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把岁前的儿童分为两个阶段,0~3岁、3~岁。第一个阶段,儿童的心智形态是成年人无法介入、无法产生影响的;而到了第二个阶段,其心智形态是成人可以介入的,但必须以某种特别的方式进行[]20。3~岁阶段的幼儿基本处于幼儿园保育阶段,该阶段是建立在0~3岁的保育基础之上的,处于幼儿能够接受教育与引导的初期到法定入学年龄之前这一阶段[7]。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幼儿”概念为3至岁或7岁这一学前时期的儿童。
1.2 健康
“健康”已经逾越了“躯体没有疾病”的狭隘理论,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bi-psyh-sial edial del)”的三维健康评价体系。本研究所涉及的健康也同样包括幼儿生理、心理与社会适应三个维度。
1.3 生态学
“生态学”(Elgy)是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 .Haeel)在18年提出的,他把生态学定义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关系的一门科学[8]。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形态[9],人类生态学作为生态学的一个分支,是由社会学家奠定了它的基础,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把人作为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进行研究。本研究中的“生态学”亦是指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条件下幼儿个体健康与自然、社会、家庭环境中各因素的相互关系。
2 现代社会的藩篱与束缚:幼儿健康成长的困境与危机之源
现代社会人对自然界的掠夺与破坏,造成了人类社会内部人际关系的紧张与冲突[10],当今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幼儿作为人类个体成长的必经阶段,他们亦难超越现代社会冲突所带来的困扰,加之其成长阶段的特征,孩子们健康所遇到的问题凸显。
2.1 温室里的花朵
物质生活的丰富使人们不再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与自然界抗争;交通工具的发达减少了双腿长途跋涉的机会;机器的革新正逐步解放人的体力劳作;医疗水平的提高帮助人们获得更多战胜疾病的机会。社会的发展从一方面来说“正在使人脱离自然”,丰富的物质和发达的科学技术已成为人们摆脱原始自然的支撑条件[11]。成年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在“人造自然”与人文关照双重呵护下的幼儿,他们更像是生长在温室的花朵。为了使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免受伤害,家庭、幼儿园、社区保安等对他们采取全方位、无间隙的多重监护;为了使孩子们的躯体尽快康复,抗过敏药、抗生素等齐上阵,直到把病症全部拿下为止;为了更好地释缓幼儿在与同学(或玩伴)游戏或交流中出现的矛盾,家长、幼儿教师或监护人总是出面,利用自己的权威进行调解。幼儿的生活场域完全被成年人所遮蔽,无论是自然界的严寒酷暑、风霜雪雨,还是人文生活中的困难、挫折,敞显在幼儿周围的环境总是风和日丽、一帆风顺。孩子们生活在这种超自然的环境里,如同温室里的花朵,享受着阳光的沐浴,充实的给养与适宜的温度。
生活环境的安逸对幼儿的成长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为孩子们提供安全、舒适的成长环境;另一方面也会逐渐消解幼儿在自然界的生存能力,退化机体自身的免疫力,禁锢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人类的思维方式与生存能力是在不断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与提高的,而不是先验或既定的,因此,要使孩子们尽快地健康成长,就必须让他们更多地与周围环境进行交流。衣食无忧的现代社会,幼儿远离了“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的田园生活,同时也缺失了学习劳动与亲近自然的机会。幼儿或许明白“粒粒皆辛苦”的意义,但他们却很难想象出“锄禾日当午”的艰辛画面;每位幼儿都明白自己的玩具应该拿出来与伙伴们一同分享,但真正能做到与其他小朋友主动分享自己心爱玩具的又能有几人?幼儿都曾被灌输“不要独自与陌生人交流”,但又有多少孩子能经得起陌生人的哄骗?脱离了自然与生活的抽象伦理说教,对于幼儿心灵的影响犹如温室大棚遮护下的花朵,看上去娇美艳丽,却无法健康成长于真实自然之中。
2.2 巨人的奴隶
婴儿从出生时的一无所有开始,逐渐开辟走向成人的道路,他们把成年人当作自己的主人,要无条件的服从;成年人给予婴儿生活的必需品,同时也负责对他们的监护。当婴儿成长为幼儿之后,他们便发出更多的独立思维与行动的能力和诉求,但众多成年人仍延续对待婴儿时期的那一套理论来对待幼儿。该理论包括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来教育幼儿,从自己的角度来区分幼儿的善、恶、美、丑;幼儿园在针对幼儿的教育过程中,也同样制定出一套“权威”的理论,其包含“命令、禁止、惩罚和威胁”的办法[]3-,一些家长亦对此种“严加管教”的方法给予赞同、支持。然而,在这种保育环境下,幼儿原本顽皮的天性被压制,原本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被抹杀,强迫他们按规定的姿势坐在教室里学习。美国著名幼儿教育家丽·凯茨(Lillian atz),曾在一次针对中国幼儿教育的调研中目睹:40多个3岁多的孩子耐心专注地坐在小椅子上40分钟,观看他们同学的舞蹈表演。该课程结束后,她怀着疑惑的心情请教该班级的教师,孩子们怎么能够做到长时间专注于表演?该教师回答:“是我们要求他们不许乱动,认真观看!”在这位教师看来,儿童不顺从好像是不可想象的事情[12]。对于来自成年人的管束,幼小的孩子们也经常尝试着使用各种方式来反抗,其中包括哭闹、消极应对、暴力等。诚然,他们的这些手段在成年人面前往往是失效的,总是被成年人高大强壮的躯体和较于幼儿更发达的头脑所控制、俘虏。在幼儿生活的环境里,周围总会出现巨人的身影,他们一方面帮助孩子去成长、学习与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巨人也管束着幼儿,常常使幼儿的话语权丧失,从事自由活动的时空被挤压,创新的思想被捋成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思维定势。
2.3 成长中的冲突
生活中,虽然要求家长爱护、尊重孩子,孩子学会理解家人,使他们能够和谐相处。而实际上大人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常常是不和谐的,甚至矛盾的[13]。当代幼儿与成人的冲突产生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首先,日益紧张的成人工作环境与儿童世界不相协调,成年人对生活中许多复杂的工作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去完成,如果让这些成年人停止手中的工作,来适应儿童的生活节奏与精神视野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原始人的平静、朴素生活,幼儿在那个年代可随意找到精神的庇护所,他们与从事简单工作且生活平静安宁的成人相接触,周围是家畜、草屋与真正的自然界,在那里他们可以任意触摸周围的东西,也可以做自己的工作而不必担心遭到反对,当他们困倦时,可以躺在树荫下、成人的旁边休憩。然而,现代文明逐渐地把自然环境从幼儿身边收走,快节奏的成年人生活成为儿童健康成长的障碍,幼儿不再进行他们原本从事的自然活动,他们的“王国”已不再是这个世界,他们成长中的意识甚至处处与这个社会相矛盾,就连与父母朝夕相处都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另外,当下“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同时,也使过去彼此熟悉的区域社会不见了,甚至邻里之间都不相往来,孩子孤立没有朋友,区域社会培养孩子的功能缺失,使幼儿局限在亲人或幼儿教师的独立监护下活动。近年来,由于国内几起针对孩子们的恶性事件,幼儿人身安全的问题更是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如:幼儿园接送制度的严格规范与警卫人员岗位的设置,合格校车的强制使用,以及社区警用器材配置的增加与更新等。然而,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孩子们人身安全得到保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幼儿自由、健康的成长。此外,信息传播的途径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拓宽,但色情、暴力等传播内容对幼儿健康带来的危害也在逐步增加。概而言之,现代社会在攫取与占有物质和科技的同时,亦消解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淡忘了幼儿健康成长的本真需求。
3 幼儿健康危机的突破:后现代主义的生态学取向
后现代主义是对科学、发展之弊进行理性反思的一种社会思潮[14]。它认为,现代社会突出个人主义的核心地位,而消解了个人与自然、社会与历史之间的关系[1],现代社会的这种思维与生活范式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了及其严重的后果。它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传统社区结构,削弱了人类自然发展中的人际关系,孤立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上来看,前者生发于后者并从后者中汲取养分,而又试图超越后者。可见,后现代主义是在思想观念上反对现代主义的部分范式与成规,而并非对后者的全盘否定。生态学亦属于后现代主义范畴,是在现代文明的场域内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视域来管窥与扬弃社会发展中的弊端。后现代主义范畴下的生态学范式,必将成为现代社会中实现人类健康促进的那扇窗户。幼儿在现代社会场域中遭遇的健康危机,也必然要诉诸于后现代主义的思绪来求解。
3.1 突破禁囿:幼儿的向自然生成
马克思认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其之外没有对象,他就不是对象性存在物[1]。人必须以周围环境为对象来表现自己的生命,必须在与自然的交流中获得自由。然而,在布科金看来,自然不仅是人类精神和自由的发源地,而且还是人们获得自由的藩篱与禁囿[17]。具有肉体与心灵的人类,自从出生前就做好了在地球环境里生存的准备,他们作为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其它动植物一样是受恩浴与制约的存在物[1]。首先是肉体,其构成人的生命,是人健康生活的物质基础,人不可能像笛卡儿认为的那样“我思故我在”,而只能是我“在”故我“思”,肉体是思维、精神与灵魂的寓所。人类社会存在的性质应该被看作是对自然世界的顺应,而不是对于自然界的征服。万物并育而不害,“天、地、人”共处同一生态系统中,人源于自然,系“天、地”的产物之一,并与其和谐共存。同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即与人相比,“天、地”具有亘常的自然性。人只有做到向自然而生,才能健康和谐沐于天地之间。幼儿也同样需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向周围表现自己的存在,表达自己能够融入自然,并与周围环境和谐发展。然而,当下社会的幼儿摆脱了“缺衣少食”“舍不避风”时代的困扰,却又被阻隔了与自然环境的自由交流,以至于陷入物质过剩的“精神饥渴”与“选择性恐慌”的禁囿之中。
突破当下物质与科技对幼儿亲近自然所制造的藩篱,向自然回归,才能更好地汲取环境的营养,从而使孩子们获得更健康的成长空间。高楼大厦的“巢居”时代更替了“阡陌交通”的田园生活,同时也减少了人们亲近自然的机会;快速的交通工具方便了人们的长途旅行,同时也剥夺了人们体能锻炼的机会;医疗水平的进步与医药科技的发达协助人类战胜了越来越多的病魔,同时也使人们自身的免疫力逐渐下降。当下,发达的科技与丰厚的物质所裹挟的“熵”,数倍于成年人地聚焦在幼儿身上。栖居在天地之间的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就应向自然生成,与自然浑为一体”[18]。幼儿亦不例外,他们既然生长于自然之间,就要接受自然的挑战与威胁。成年人需要做的是帮助幼儿与环境建立关联,满足他们向成年过渡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全部要求。游离于自在世界之外的幼儿,期于获得健康成长机会,必然要在人类世界中汲取“自然”的元素,要让孩子们更多地摆脱成年人的禁囿,走出人造“温室”,去掌握独立生存的技能!还是要从幼儿吃饭谈起,恐怕诸多家长,尤其是隔代家长,在养育孩子过程中最头疼的事情莫过于他们的吃饭问题。每每饭时,餐桌上汇聚东西方美食,色香味俱全,家长们常常为让孩子多吃一口饭而轮番上阵,采用威胁、哄骗、讲条件、说道理等各种手段,可谓费煞心机,却效果不佳。很多孩子在这种填鸭似的喂养下,形成了偏食、厌食等习惯;还有一些孩子吃成了小胖墩。作为动物,食物往往是它们追求的重要目标,因为进食是任何动物从外界摄取营养的主要途径,也是人生存的根基。如若机体无法获取足够的营养,那么他将不能健康地存在于自然界。然而,幼儿为何违背了动物进食的自然界规律?诚然,并非幼儿违反了自然规律,而是成年人把幼儿“生物性”的生活环境打破了。当成鸟刁着寻觅的食物飞回鸟巢时,里面待哺的一群幼鸟叽叽喳喳喊叫着去冲抢,自然界竞争的残酷性迫使它们去抢着吃。而幼儿则不然,在家里,他们几乎没有来自同龄人的竞争,家长“一切为了孩子”的理念给孩子提供各种安逸、便利条件的同时,也正在剥夺着幼儿在自然界生存的能力。历史取法于自然,社会取法于自然,人类同样亦是取法于自然,然而幼儿却生活在一种“超自然”环境下,束缚着他们独立的社会交往欲望。只有让幼儿们的生活真正取法于自然,亲近于自然,其才能突破“伪自然”的禁囿,获取自身健康成长的场域。
幼儿阶段是每一位成年人必须经历的特定时期,因此,幼儿所面临的问题亦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同样,幼儿的自我实现,意味着不仅是幼儿,还包括人类甚至所有生命的潜能实现。“谁也不能获救,除非大家都获救”[19],是生态学家对自我实现过程的形象概括。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越是丰富,越是保持接触生物的多样性,其自我实现就会越彻底。幼儿亦然,应该让他们在现代社会嘈杂的环境中亲近自然,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而获得健康的身心。
3.2 由安逸到适宜:环境的向幼儿生成
幼儿保育体系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强调环境的重要性[20]。幼儿个体是在真实的自然、社会环境中成长、发展的。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社会环境,但这一改造的施动者基本为成年人群体,虽然在改造过程中亦会涉及到与幼儿相关的内容,然而,在这些内容的改造上并不是体现幼儿的智慧与需求,而是成年人的一厢情愿。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文明过分陶醉于改造与征服自然界的成就,但是,对于每一次这种成就,自然界又都加倍报复了我们”[21]。幼儿时期是其一生中健康肌体形成与性格、习惯、思维方式养成的关键期。在这段时间内,对幼儿的影响与教育哪怕有一点偏差,就会出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惨痛后果。然而,成年人总是把自己身边的幼儿当成直接改造的对象,他们对于体现在幼儿身上的表象改造成果沾沾自喜,却遮蔽了幼儿健康危机的呈示。孩子们囿于社会、自然、物质等多重环境下,这些良莠不齐的环境是导致幼儿能否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如何营造一个适宜幼儿健康成长的环境,是我们当前思考的重点。
自然界中的阳光、空气、水、植物等都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条件,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幼儿肌体健康的保障。然而,近些年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发展,致使天空阴霾、水质乌黑、绿地沙漠化。化学物质、电离辐射等在幼儿身上表现出更高的易感性与高危害性[22]。一方面,由于幼儿身体处于快速生长发育阶段,部分器官与系统对外界毒素的抵抗力较差,容易受到影响,而一旦污染源潜入幼儿内分泌物质,将发生持久的或不可逆转性的损伤[23]。另外,由于幼儿的生存时间一般长于成年人,环境中的污染物一旦侵入机体,将影响他们的生长发育甚至引起慢性病,危害期较长。近年来,幼儿白血病、癌症、哮喘等疾病的发病率持续走高[24],与环境污染的加剧不无关系。另据统计[2],在北京儿童医院就诊的白血病患儿中,90%的家庭在半年之内做过装修。由以上案例可见环境对幼儿健康威胁深重,营造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为孩子们及其子孙后代提供良好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当代人责无旁贷!
家庭、幼儿园、社区乃至整个社会均应尊重幼儿成长过程中的身心特征,创设适宜幼儿锻炼、成长的物件环境。即使在一个物质较为丰富的幼儿家庭里,除了玩具之外,也几乎很难找到属于幼儿自己的东西,如洗脸池、书架、沙发、衣柜等等;社区、超市、公园、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的服务性区域与器物,多是属于成人的财产,是按照成年人的身材比例设计、安装的。除专门盈利性的娱乐场所外,公共空间的器物设置很少能考虑到幼儿独立使用的适宜性,以致很多物品对幼儿来说都成为禁物,不能使用,甚至不可触及。成年人经常绞尽脑汁去帮助孩子,结果却像“襁褓”一样裹住了孩子,最终事与愿违地影响了他们自然的发展。譬如,许多幼儿园或学校为了防止孩子们把桌椅弄乱,而把其固定在地板上;再如家长担心孩子打碎碟子,而使用铁质器皿。这些障眼法并没有给孩子太多的帮助,反而阻碍了孩子的发展。幼儿的成长应是一个渐进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不断地与周围的物件环境进行交流,直到他们像成年人一样掌握器物的特征及其使用规律。因而,根据幼儿的年龄、生活与性格特点来不断调适其周围的物件环境,让孩子们尽快认识与操控身边的器物,对处于逐变中幼儿身心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3.3 强制保育向自为存在的回归之路:幼儿人文环境的救赎
强制性的力量成了一切变化的基础是现代思维范式的一个灾难性特征[1]。面对现代社会的困惑,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用强制性的力量改变一切”的思维范式存在的问题。该种强制性聚焦在成年人对孩子们保育之上,表现为把孩子们从自由成长的环境中剥离,由此所产生的危害与人类僭越本真自然所带来的后果无异。
成年人应以“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原则,来处理、解决幼儿成长中的问题,让孩子们获得更多的自为存在的场域。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始于一种自为的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超自然的环境,即文化、社会环境,同时,人亦成为文化的存在,社会的存在[2]。然而,文化与社会均是以数理与思维逻辑结构为基点理论,由概念原理与规律法则构成的严谨世界[27],幼儿总是在成年人的文化与社会经验遮蔽下出场,幼儿成长的环境无处不笼罩在形形色色的规律与概念之中。这些超自然的规律、概念在观照幼儿保育理论上主要表现为同一化与恐慌性。同一化的理论把对幼儿的保育近化为现代工业文明中的流水线生产,不同的阶段务必严格执行各阶段成规性的保育方式与方法,成批的孩子们在这一流水线上按照预期的既定理论发展成长。然而,这种现代文明下的保育理念逐步显露出对人文精神的漠视。对于人类的教育,其根本宗旨是唤起人自由自在的人格境界,激荡起心灵深处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非像工业文明那样批量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振聋发聩,“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标语更是不断充斥着人们的视听。这些言论一方面提高了对孩子们教育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幼儿的体质健康、性格习惯、智力水平等等,均成为了成年人保育恐慌的生发之处。在种种“恐慌”浸染之下,成年人保育幼儿的方式与方法逐步偏离自然的轨道,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偏离也使得幼儿生长在超自然的人文场域内,并深受其害。孩子们渴望自为的空间,同时也需要属于自己的成长方式。美国教育学家杜威(.Deey)认为:儿童世界不是一个规律的世界,而是一个具有他们个人兴趣的世界[28],在幼儿成长的过程中要充分挖掘幼儿自身的能动性。人类从出生开始就在不停地忙碌着,不要认为工作仅仅是成年人的事情,幼儿同样需要工作[21],只是成人与幼儿通过工作所构造的目标路径不同,前者的工作系营造自身与整个人类生活的环境,而后者工作目的是使自己逐步成为健康的成人。基于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此动态视域来看,孩子们工作的意义甚至要超过成年人。当然,尊重幼儿的自在空间并不是采取一味地纵容或妥协的方式来满足孩子们的一切诉求,而是尽可能地提供一个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环境,构建一个幼儿与成人、幼儿与幼儿之间自由交流的空间平台,使他们彼此之间进行相互适应的训练,而不是采取逐本求末、揠苗助长的方式,更不可陷入形而上学式的教条保育之中。
4 结语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于人类生活环境舒适程度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同时亦为人类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幼儿是人类个体成长的必经阶段,也是人类健康身体与习惯生成的关键期。如何突破社会发展之于幼儿健康成长中的“二律背反”(Antinies),只有诉诸于后现代主义的思绪与智慧。后现代主义范畴下的生态学取向是当代幼儿健康促进的必然结果与发展趋势。学术研究本身就是观察客观存在的一个视角,通过此视角可显豁问题与针砭时弊,亦可提出对策建议与突破策略。本课题突出生态学角度与幼儿健康的关系,警示现代文明之熵对幼儿的危害,对抗工业文明对孩子们健康的威胁,并以期引起更多地相关研究,来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
- 上一篇:学前儿童使用手机媒介的影响及对策
- 下一篇:幼儿园中班中秋节环境创设初探